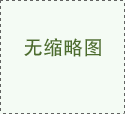陕北剪纸起始于陕北文化的真正发源地——榆林,然而陕北剪纸却因对于艺术的后知与先觉的——延安人而抢先占领了书面传播的权利,一而再、再而三地编辑出版陕北剪纸方面的书籍,被人们错位地理解为陕北剪纸似乎只出在延安。榆林人也曾出版过陕北民歌、陕北民间故事等方面的集子,惟独似乎忽略了这一代表陕北文化典型现象的文本图式——剪纸。这是有意的淡忘抑或历史记忆的丧失?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榆林人自己的觉醒,张芳主编的《榆林剪纸辑录》,第一次以榆林剪纸人的集体面孔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它是历朝历代陕北人的春节里无数个窗户闪亮世界的历史缩影,是从黄河九曲十八弯的褶皱到起伏流动的毛乌素沙漠边缘无数把剪刀红纸世界的再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平面的图画艺术的记录,透过这些平面世界,我们会更多地体察陕北妇女内心世界的强烈涌动。在中国更在陕北,旧时女人的外部世界被庞大的意识形态、被无形的夫权社会霸占得所剩无几,但永远无法遮蔽的是她们的内心世界,“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的时代语录运用在她们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活学活用”,她们无奈到不敢把眼泪把愤怒把喜欢写到脸上,她们巧妙地转换形式将丰富的情感世界暗含在一把剪刀与红纸里。表面看,这是一种扭曲的艺术,但正是由于这种“陌生化”才有了“隐喻”、“反讽”等一系列艺术的形式真谛在先于西方现代派艺术若干个世纪而先觉地发生了。剪纸,并非陕北独有,剪纸是普天下妇女运用她们剪衣服的工具裁剪实用世界的同时也忙里偷闲地活跃她们内心世界的语言符号,但陕北的剪纸更有别于其他地域的是,它的纯色大红与自古而然的内容与形式整合的一脉相承,虽然印在集子里的是黑白底质,但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会熟稔地读出那些大红大白来。
集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列在最前,实际上应该算作“附录”类的东西,它是现代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对陕北剪纸“感言”类的体悟文章,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文章。事实上,要从理论上把握陕北剪纸的真正意义破译它的内涵恐怕很难,或许永远无法企及,我们只是隔岸观火地以现代人的思维去揣摩古人尤其是妇女世界的冰山一角。第二部分不管是旧时藏品还是传统剪纸作品,其实都是祖先的剪刀记忆,这应该是我们永远视为珍品并将以此溯源探求真正剪纸艺术的活化石,没有它们,我们现代的剪纸将一文不名,西方人中国人之所以喜欢剪纸大多是奔着剪纸的内容深蕴与形式的原始反叛而热爱的,不是我们泥古而不拔,不是我们只求继承而不敢创新,我们提倡的是在根的基垫上的历史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切忌抛离了根的存在而将剪纸变成另外艺术嘴脸的无土栽培。由此,对于第三部分的创新作品,我们就会发现那里边很大一部分祖宗基因遗传的无法剥离,她们或从奶奶的老花镜或从母亲的大粗剪里流淌下来的血脉记忆,她们是历史的薪火相传者,是陕北文化深层土壤里生长着的传统山丹丹花。
眼光,是编辑者的重要素质。张芳同志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行政领导,她的眼光是俯瞰榆林大地的全方位视角,行政文化领导的得天独厚,使她几乎跑遍了榆林的每一寸土地,她的整体扫描规避了一般艺术工作者的足迹范围所限,她入乎绥米神定之内又能出乎蛇盘兔碗扣鸡之外,高视角大面积地囊括了榆林剪纸的各色各样,以集体的形式整合亮相,委实是难能的一大文化业绩。张芳更难得的是她自己就是一个剪纸艺术家,在中国在陕北,有大学毕业的文凭有市级领导的级别而又同时是一名剪纸艺术家的身份,恐怕前无古人。正是这种自身浸于其中深解其中之妙其中之苦其中之乐的人,编这样一本集子,恐怕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为政与为文是两重世界,但为政之余为文,是对政事繁杂的缓释,是对政事理性秉直的迂回。为文不忘为政,是“以人为本”的情感参与,是艺术情怀人性感召的政策胶合,何乐而不为呢?
感谢张芳,她的《陕北剪纸辑录》,为那些从小生于斯长于斯只从母辈剪刀里汲取营养的剪纸人提供了另一角度的参照系,让她们洞开另一窗口看到了别家窗户上的红色世界。使我们这些钟情陕北文化研究陕北文化的人士省却了多少翻检之劳多少脚板之苦去踏访那些坐在炕头近在眼前却无法确认为艺术家的妇女同志。我们最欣喜的,还是它的第一次,榆林剪纸真正集体亮相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