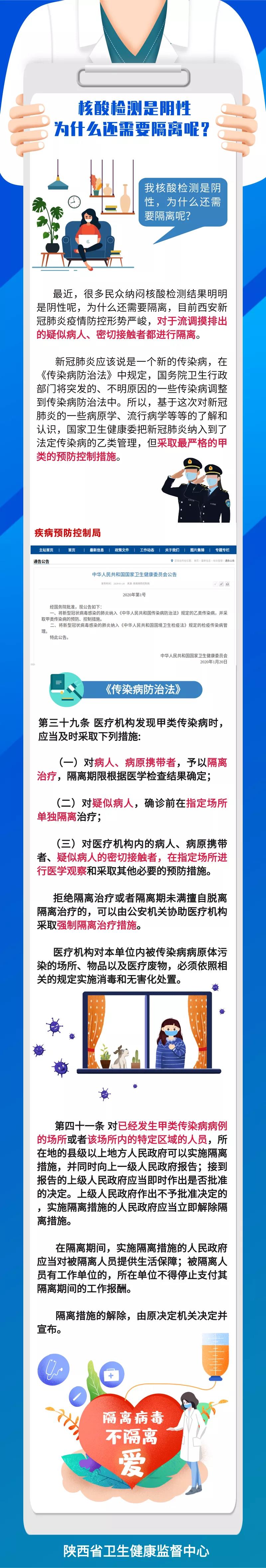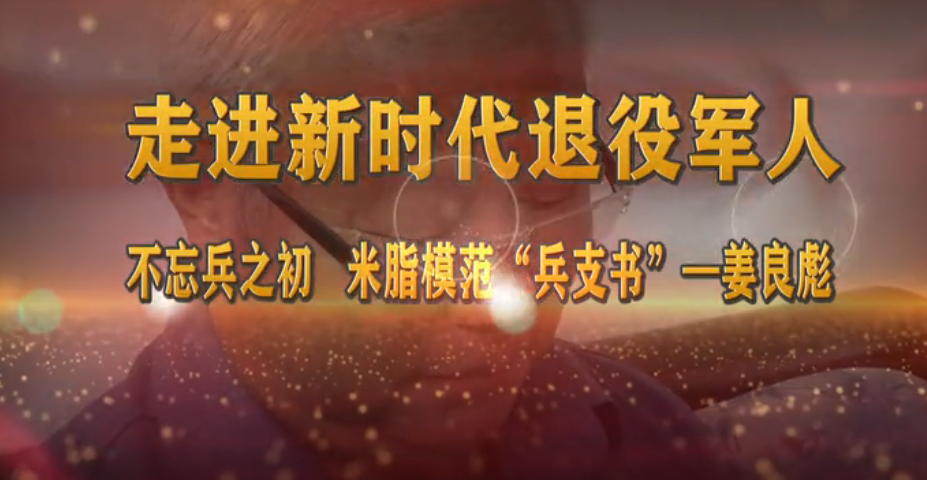从历史深处走来的秧歌,从未停顿过脚步,从原始的巫术诉求逐步进化为吉祥祝愿。而那些巫术中得到的虚幻纹样逐步演变成规矩吉祥图案——秧歌场子。
在秧歌场上,伞头右手举伞,左手拿着能摇出声音的可以驱除鬼神祛病禳福的“虎撑”,带领队员,踏着锣鼓唢呐的节拍,按一定的规则,一定的路线,边扭边走,走扭结合,到一定的位置,该向左转,他转身向左,退后一步,再右跨一步和后面的队员面对面,笑脸相迎,四目传情,旋转向前迈步,形成秧歌场图中的一个拐角,称之为安角子,后面所有的队员到此处,以同样的步代、同样的旋转转角子,就这样形成一个个拐角和一条条人流线条相连,形成了规则的秧歌场子阵图。伞头要对整个场图和每个角子的位置做到心中有数,整体构图清楚。这样角子才能安的准,移动小。当伞头安好所有的角子,走完整个场图时,把所有秧歌队员都安在了角子和人流线中时一个吉祥的秧歌阵图就形成了。那些用人流构成的线条和人们旋转的角子,蜿延、曲折、流动不停,像陕北那西来北上南下东去的黄河,但不管怎样流动、翻、滚,整个阵图始终不变。这就是陕北秧歌的大场图。
文化人类学家们有一个基本认识:人类文化来源于远古时期的巫文化。人类从懵懂时期就开始追求外力保护,从未放弃。那些线条图纹的雏形在巫术时代被认为具有巫的能量。这种巫文化一直流传至今,后世各种原始几何纹样的综合使用,变革,以方带圆,四面八方的主流结构,造就了程序化的各种盘长图形。巫符纹样赋予了道家、佛家的信仰内涵,由于巫术时代的信仰遗传,让这些图纹具有了让人信服的吉祥含义。细观现在各庙会上所发放的驱邪祛祸,祈福保平安的各种神符、门符、护身符 和阴阳 先生画的咒符图案。这些图符和出土的土陶古瓦中的吉祥图纹几乎一模一样。再看我们秧歌场图中的“龙摆尾”、“拧麻花”、“蒜辫”、“双蒜辫”等图阵和那些符中的图纹很相似,可以相信这些秧歌场图就是从古时的巫术咒符图纹中逐步演变而形成的。
“大豁四门”这个场子由两支队伍重复四圈才能完成,走成圆圈后,两支队伍交叉后并排走圆的直径,以蛇脱皮的形式折返,走完东、南、西、北四个交叉点的豁门。“史记、封禅书”的注引里“历鬼为蛊,将出害人,旁祭于四方之门”说的是一种傩祭仪式。“大豁四门”场子与一种三角雷纹组成的吉祥团寿字造型一致,这种造型可以从汉代呈十字图形的变体云纹篆上,新石器时期马厂型彩陶的符号纹样中找到线索。现在秧歌场图,单蒜辫、双蒜辫、金龙摆尾、乱点兵、枣核开花、二龙吐须等都是以从“大豁四门”中演变而来的吉祥图阵。有些场图名字中就寓有吉祥之意,如:四面八方、神仙推磨、大彩门等。巫术时代的咒符纹样,直接沟通天地人文,作用于驱邪祛恶之祈求,如富贵不断头纹样,寓意绳索、以缚鬼神,而拧麻花、龙摆尾、万里长城,十二龙灯等都是这些咒符的变形。
秧歌场图的蛇盘蛋和拜四方(又叫单十二莲灯)则是仿佛家的八害之——“盘长”图纹而形成的,像征四环贯通,一切通时、连绵不断、事事通顺。陕北人把盘长作为秧歌场子的重要因素。将盘长的基本图案演变后出现了许多让人叹为观止的各种秧歌场子。“十二连城城套城”可理解为四面八方之中套入四个小城,而这实际上就是常见的“方胜盘长”,“双十二莲灯”实际上是“套方盘长”,而“十二莲灯灯点灯”与花团锦族的“万代盘长”同宗,“单葫芦”是葫芦型的“万代盘长”,而双葫芦走的是吉祥图“双盘长”、“十二莲灯灯套灯”四十四个角子正是“四合盘长”。
吉祥图案,沟通天地人神,寓意驱邪扶正,除恶祛病,更多地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寄托。伞头带领人们,为了一个精神目的,共同走出由巫术中的咒纹和道教,佛教中的吉祥图演变而成的秧歌场子,那是一种红火,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传统信仰背后的文化诉求和它所表现出来的信仰仪式。它能带来沟通天人的社会功能和传代农耕的社会秩序,这是它的本质所在。